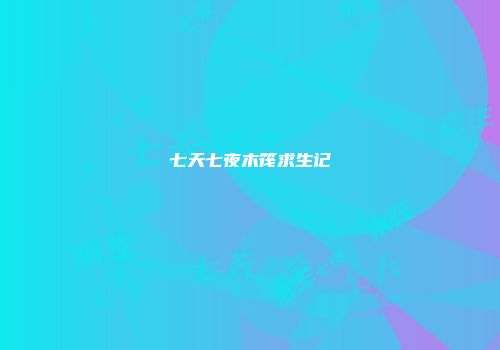海风裹着咸腥味扑在脸上时,我正攥着用海藻纤维捆扎的竹筏缆绳。脚下两米长的木筏在浪尖颠簸,防水布裹着的工具箱里只躺着鱼钩、伞绳和一把瑞士军刀——这是我能带走的全部现代文明痕迹。
老渔民陈叔听说我要玩真的,蹲在码头抽完三根烟才开口:「带三样东西:椰子、珊瑚碎、你的脑浆子。」后来才知道,这三样分别是淡水来源、捕鱼工具和智慧储备。
用六根碗口粗的毛竹扎筏时,我特意留了三个玄机:
第二天正午,喉咙像含着块烧红的铁。海天交界处飘来的乌云,让我想起陈叔教的「三层滤水法」。
| 工具 | 用法 | 收集量 |
| 防水布 | 折成漏斗状接雨水 | 3L/小时 |
| 竹筒 | 内壁抹椰肉吸附盐分 | 0.5L/次 |
| T恤 | 拧出布料吸收的雨水 | 200ml/件 |
记得在浪头打来前把储水槽盖好,我有次贪多接了五升水,结果全喂了太平洋。
挖个沙坑埋进湿海藻,扣上铁皮罐子,烈日下能收集蒸馏水。有次我异想天开塞了几片生鱼,结果得到带着腥味的淡水——倒是补充了盐分。
第三天饿得眼冒金星时,发现鱼群在木筏阴影处纳凉。用伞绳纤维编的渔网总被咬断,直到我把珊瑚碎片磨成倒刺。
生吃海胆时被扎得满嘴血,后来学会用两块竹片当筷子夹着吃。最惊喜的是在礁石上抠下藤壶,煮熟后有鸡肉的香味。
第五天的暴风雨教我做「人」。三米高的浪头砸来时,临时搭建的三角棚瞬间散架。痛定思痛后,我琢磨出动态锚定系统:
棚顶改用可开合的棕榈叶编织板,雨天闭合储水,晴天打开通风。有次半夜被章鱼砸醒,才发现该加个防坠网。
最后36小时遇到离岸流,木筏以每分钟60米的速度漂向深海。我摸出瑞士军刀里的指南针——其实是扣子蘸机油自制的——借着星象修正航向。
当救援船探照灯扫过来时,我正用鱼骨磨成的钩子修补渔网。浸透盐渍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着:「第七天,捕获飞鱼两只,蒸馏水300ml,棚顶漏雨已修复。」
海平线泛起鱼肚白时,船长递来的矿泉水尝起来有点甜。我偷偷倒掉半瓶——舌头早就适应了带着海藻味的淡水,反而喝不惯这种「没有故事」的水了。